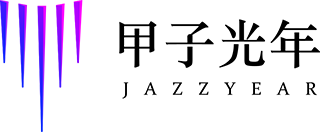當微軟CEO納德拉抱怨,GPU因缺電而閑置時,谷歌、英偉達和SpaceX正在制定昂貴的太空數據中心藍圖。但在他們行動之前,中國有一家公司已經發射、組網并開始商業運營。
“我們有海量閑置的英偉達GPU,但他們只能躺在機架上,因為根本沒有足夠的電力去點亮他們。”
微軟CEO納德拉最近的這句驚人言論,向市場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:AI競賽的終極瓶頸,已經從芯片供應轉向了最基礎的資源——電力。
這背后是冷酷的財務焦慮。在AI的“淘金熱”中,英偉達的芯片迭代速度太快,從H100到Blackwell,“有效保質期”越來越短。對于手握價值數千億美元GPU的科技巨頭而言,電力每延遲一天,這些昂貴的硬件資產就在無聲地“蒸發”,還未創造利潤,便已逐漸要過時。
但AI對“無限”算力的追求,正撞上地球有限的電力、水和土地資源的“物理之墻”。
這場危機正迫使巨頭們啟動昂貴的“B計劃”。在地面,亞馬遜和谷歌,已開始布局小型模塊化反應堆(SMR),試圖通過小型模塊化核反應堆來解決問題。
另一個更激進的選項則指向太空——英偉達和谷歌這些科技巨頭們,都在搶著把芯片送“上天”。
但令人驚訝的是:在這場關乎AI未來的新競賽中,第一個沖過起跑線的并非硅谷巨頭。
一家名為“國星宇航”(ADASPACE)的中國公司,早在2025年5月14日,就已成功發射了全球首個太空計算衛星星座。這并不是一次簡單的技術測試,而是一個已經實現商業化、正在太空中為客戶運行AI算法的算力網絡。
在全球AI版圖重構之際,中國是如何在“太空算力”這一關鍵高地上,悄然取得先發優勢的?這對未來的技術格局意味著什么?
1.硅谷的“太空B計劃”
納德拉對電力短缺的抱怨,是日益緊迫的行業危機。為了擺脫“地球物理墻”,硅谷巨頭們的“B計劃”——將數據中心送入軌道,正從科幻變為嚴肅的工程藍圖。
谷歌的“捕日者”(Project Suncatcher)計劃最為詳盡。它的目標是在軌部署自研的 TPU芯片。根據谷歌的論文,它設計了一個由81顆衛星組成的計算集群,在1公里半徑內以100-200米的間距緊密編隊飛行。
這是一個極其激進的方案,其背后是精明而高風險的技術取舍。谷歌之所以要冒著極高風險采用100-200米的超近編隊飛行,是因為只有在如此近的距離上,才能產生足夠高的接收功率,從而允許他們直接使用地球數據中心已經成熟的、高功率的DWDM光通信模塊,以實現1.6 Tbps的高帶寬。這種設計雖然巧妙,但也極大地增加了軌道控制的復雜度。
不過在實驗室中,谷歌已取得關鍵進展:他們用67MeV質子束模擬太空輻射,證實TPU芯片的抗輻射能力遠超5年任務預期,星間所需的1.6 Tbps高速光鏈路也已在地面驗證成功。
但谷歌也坦承其計劃的“阿喀琉斯之踵”:這個計劃的經濟可行性,完全依賴于發射成本能否降到200美元/kg以下。所以,谷歌將時間表定在2年后,首批兩顆原型衛星將于2027年發射。
英偉達則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投資路線,全力支持初創公司Starcloud,這是一家新銳的創業公司。Starcloud的行動迅速:在2025年11月2日,利用SpaceX的火箭成功發射了其首顆測試衛星。
這顆衛星搭載了英偉達H100,它的任務不是組網,而是測試在軌AI推理。這顆衛星的特別之處,在于其“集各家之長”的輕資產模式:它依賴英偉達的H100進行計算,計劃在軌運行谷歌的Gemma開源模型,并由SpaceX負責發射。
盡管其最終藍圖,是建設一個5吉瓦、由4公里寬,由太陽能陣列供電的龐大軌道數據中心,并大膽預測“十年內幾乎所有新數據中心都將在太空建造”,但其當前階段仍是“原型驗證“,商業化最早也要等到2026年。
亞馬遜和SpaceX也已入局。貝索斯預測,未來10至20年內,將出現吉瓦級的太空數據中心。而馬斯克則明確表示,SpaceX將利用其帶寬達1 Tbps的“星鏈V3”衛星進入太空計算領域。
可見,科技巨頭們都紛紛發布了他們的AI太空數據中心藍圖,那么一個關鍵問題是:究竟是什么樣的危機,迫使科技巨頭們,如此一致地將目光投向成本高昂、技術未定的太空?
2.科技巨頭們為何被迫“上天”?
這些動輒耗資千億的太空計劃,源于地球上日益嚴峻的三重物理困境:
最大的就是能源瓶頸。AI正成為“吞電巨獸”。到2030年,全球數據中心將需要額外67吉瓦的電力,這相當于67座大型核電站的發電量。這背后是“時間”與“財務”的雙重錯配:英偉達芯片快速的迭代周期,與電網擴容長達2至5年的審批建設周期,形成了致命的時間差。
這意味著,當微軟和亞馬遜還在為新數據中心排隊等電時,他們倉庫里價值數十億美元的GPU資產正在迅速貶值。這迫使巨頭們需要思考更創新的能源方案。
還有散熱與水資源消耗。AI芯片的高密度運行,散熱也成為非常大的問題,而液冷技術,是在耗電量和用更多水之間取平衡,如果想減少耗電量,就會成為“耗水巨獸”。根據國盛證券的一份報告,以Meta為例,其新建的數據中心日最高用水量達600萬加侖,遠超當地全郡用水量。
最后是土地與選址困境。吉瓦級的數據中心占地巨大,在經濟中心附近選址變得極其昂貴,甚至引發了與民生爭奪土地和電網的矛盾。
在太空軌道建設AI數據中心的方案之所以可行,在于它不僅解決了能源、散熱等資源問題,還在根本上重構了數據流。
首先,它一舉解決了物理限制。在軌衛星能享受8倍于地球效率的7x24小時不間斷太陽能(谷歌數據),同時擁有-270℃的極寒真空作為完美、零耗水的天然散熱器。
其次,新一代方案也解決了數據傳輸的問題。傳統的“天感地算”模式(衛星拍照、數據下傳、地面分析)早已不堪重負。正如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堅所指出的,因帶寬限制,衛星收集的海量數據“只有很小一部分能真正傳回地面”。
而“太空計算”的范式是“天數天算”(在軌計算)。衛星不再是“數據采集器”,而是“智能分析師”。Starcloud的CEO曾生動地描述了這一模式:把數據在軌處理后,衛星只需下傳一個1KB的“洞察”(例如“一艘船在某位置正以某速度航行”),而不是數百GB的原始雷達圖像,這從根本上規避了帶寬瓶頸。
不過,硅谷巨頭的宏偉藍圖,無論是谷歌的“2027原型星”、英偉達/Starcloud的“測試星”,還是馬斯克和貝索斯的“未來十年愿景”——都還是“未來時態”。
但在這場太空競賽中,發令槍其實已經打響,當所有人都將目光投向硅谷的“未來”時,一個“現在進行時”的故事,已經在中國上演。
3.悄然的領跑者——中國公司的“太空計算”版圖
就在硅谷的“PPT造星”計劃正酣時,這場競賽的第一個“實干家”,已經悄然完成了布局。
答案不在舊金山或西雅圖,而在中國。
這家公司,就是國星宇航(ADASPACE)。它并非一家傳統的商業航天公司,核心瞄準在“太空計算衛星星座”,而非“衛星制造”。傳統的商業航天模式是“B2G”或“B2B”,出售的是衛星硬件、發射服務或原始的遙感數據。
而國星宇航在圍繞“太空算力”做事情,核心產品不是衛星本身,而是搭載了AI載荷、具備在軌計算能力的“智算衛星”。它瞄準的客戶,是AI企業和需要實時智能數據的行業,它更像是一家“星際之門的太空版”。
如果來打個比方——馬斯克是要把通信基站搬到太空,而國星宇航是要把算力中心搬到太空。
國星宇航的核心工程,是“星算”計劃。這不是一份“遠景PPT”,而是已經拿到“地契”的在軌藍圖。
首先是軌道申請。在日益擁擠的近地軌道,國星宇航已向國際電聯(ITU),申請了2800顆衛星的頻率與軌道資源。在太空競賽中,這無異于提前鎖定了未來“算力地產”的黃金地塊。
其次是發射。早在2025年5月14日,早于Starcloud的H100測試星,“星算”計劃首發星座(一箭12星)就在酒泉成功發射。這12顆衛星,均搭載了智能計算系統和星間通信系統,組網后形成了全球首個在軌的太空計算中心,總算力達5 POPS(每秒5千萬億次運算)。
此外,國星宇航的商業化速度驚人。當谷歌還在等待2027年的原型星時,國星宇航的太空算力中心已經在“接單”了。2025年9月,國星宇航宣布了全球首個太空計算的商業化案例:與A股上市公司佳都科技的合作。
佳都科技將其“城市交通大模型”算法,通過地面站注入到軌道上的“星算01”星座中。星座利用自帶的AI算力,在軌計算,實時處理廣州市的遙感影像。最終,星座只將計算后的“洞察”(如路網分析結果)傳回地面,而非海量的原始影像數據。
這場合作不僅僅是“演示”,還實現了不少“效率指標”。比如它已經將傳統遙感數據服務的響應時間,從“小時級或天級”,壓縮到了“分鐘級”。同時,由于在軌處理,也節省了90%的下行帶寬和地面站資源。
“星算”計劃首發星座只是一個開始,未來的“星算”計劃02組星座(甚至再之后的03組),也已經進入設計研制階段,由中國科學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研究員、國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長王建宇擔任首席科學家,重點突破更高速的星間激光通信技術——這正是馬斯克“星鏈V3”和谷歌“捕日者”計劃所依賴的核心技術。
4.重置AI競賽的“制高點”
AI的未來發展,正受限于地球能源和物理空間的瓶頸,這也在背后推動了一場不可避免的“太空算力競賽”。
但這場競賽的發令槍并非在2025年11月(Starcloud發射)或2027年(谷歌計劃)才響起,而是在2025年5月的中國酒泉。
國星宇航的案例表明,中國不僅在AI應用層快速追趕,更在AI基礎設施的“下一戰場”——太空——取得了關鍵的先發優勢。
隨著AI對算力的需求呈指數級增長,地球上的電力和土地資源將成為最稀缺的商品。未來,誰掌握了軌道上的“算力高地”,誰就可能在數據和智能時代掌握真正的戰略主動權。
(封面來源:AI生成)
 作者:特邀作者
作者:特邀作者
 編輯:栗子
2025-11-09
編輯:栗子
2025-11-09
 36453
36453 562
562 131
131 0
0